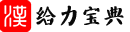《上学记》读后感
一向以出版人文社科图书著称的三联书店,前年推出了何兆武口述、文靖撰文的回忆录《上学记》。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我花了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读罢此书,让我认识到了旧中国教育的另一番景象,先前对那个时代模糊、平面的认识,一下子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原来学可以这样上!书中的很多故事在今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候甚至近乎荒诞。但掩卷沉思,不免给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启发。
何兆武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在历史学、哲学、思想史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他的英文底子很好,曾经翻译大名鼎鼎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西方哲学史》(罗素)等学术著作。他翻译的这些西方启蒙思想著作,影响了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然而,何老深居简出,低调做人,不喜欢喧哗,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会阿谀奉承,一味迎合时代。他讲真话,追求真理。在何老八十岁之后,三联书店整理出版这样一部《上学记》回忆录,在学术界、文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都很有意义。
学者出版回忆录正常的,也是值得鼓励的。可在我看的那些回忆录中,除了巴金的《随想录》外,还没有哪一部回忆录像这本书一样打动我的内心。我的灵魂被书中尘封的往事触动,我惊叹何老讲真话的勇气。讲真话似乎不难,真正写出来出版,我估计很多人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何老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民国,一个有呼吸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时代。
何老上世纪30年代在北平上小学和初中。当时虽然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是那也只是名义上的。地方军阀割据的情况还很严重。比如北平就是奉系张作霖的天下。军阀大多没有什么文化,更没有什么鲜明的政治理念,他们只相信枪杆子,不怎么买国民党的帐。所以南方国民党的很多教育政策,到遥远的北平难以实施,国民政府对于北平的教育控制,可谓鞭长莫及。奉系整天想的是地盘和银元,对教育没有兴趣。这样一来,对于教育来说,可谓是得天独厚的机遇。总的来讲,在那个时代的北平,教育的质量是很不错的,并且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大。在中小学的食堂,花很少一点的钱,就可以吃饱三餐,而且有荤有素。中学的主要课程是国文、英文、数学。由于国文大家都会,考试时分数差距不大,主要的竞争在英文和数学方面。这不免和今天的情况有点像。可是,那时候学习的课程比现在少,学生的学习压力也不算大。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的政治气氛空前紧张。但就是在国难之际,国民政府也没有放弃教育,学校开始南迁。学生和老师一起走,当然,有一些年轻的老师和学生投身行伍,加入到抗战一线的行列。当时南下的铁路线已经被日本鬼子切断,人们先坐船出海,然后在山东登陆,坐火车到汉口,再坐汽车到长沙,本来几天可以走完的路程,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想象,那么多的人南迁是何等壮观的场面。用何老的话讲,1937年七七事变后是中国最大的移民潮。何老辗转长沙、贵阳继续念中学。在北平一个富足的城市生活长久了的人,在落后的贵阳,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就在大后方贵阳上中学的时期,何老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后来,何老到昆明,就读于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当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忙于抗战,对这个在西南边陲的大学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太多政治形态上的管理。很多年后,从这所大学里走出来的毕业生,在文学、哲学、理学、工程技术方面做出了很多骄人的成绩。西南联大作为临时组建的大学,办学条件和抗战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教室和宿舍都是泥巴糊的,吃的很差,还定量,师生吃不饱。学生除了上课,业余活动很少。此外,学校有一阵子经常遭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都认真地学,老师认真地教。书中写道,飞机轰炸的情况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校长梅贻琦先生,总是不慌不忙地拿着一把伞,从容地指挥师生疏散。在疏散的人群中,当时历史系学生吴晗跑得很快。
西南联大有一大批声名海外的大师,如闻一多、沈从文、华罗庚、周培源等等。也许是抗战困难时期,联大在招生人数方面也很少,全校5个大的学院加起来才1000余人。这样小规模的招生,是今天的大学不敢想象的。当时,报考机电、经济、是热门,哲学、历史、政治是冷门。这种现状到今天还没有改变,并甚至变得更加糟糕。那时候一个专业最多招生的20多人,最少的像哲学系,一年有时候才招2人!学生人数少,上课人数也就少,往往一门课,选修和必修的同学加起来才10来个人。其中居然还有人逃课。当时,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有时候才2个学生来听。即便听课的学生很少,老师也是认真的备课,很多老师的教案,后来都成为中国经典的学术著作。学术成就突出的老师,有的很会上课,有的不太会上课,课堂气氛一般。看来学术成就和会不会上课没有关系。再则,当时理学院的很多课程,由于教材是美国原版引进的,老师为了上课的方便,直接用英文授课。我们当今大力推广双语教学,其实在70年前的中国的大学就绘声绘色地开展了。
在西南联大,教学中还有一些突出的特色。那就是学校给老师很大的自由度。老师想采用什么形式,什么教材,学校没有权利干涉。有一个老师讲授世界历史,一个学期下来,连古埃及史都没有讲完。几天看来,这样的老师是教学事故,很有可能下岗。课堂上,学生可以对老师讲的内容提出质疑,对一些学术问题,可以展开探讨。周培源先生的课堂上,经常有一个学生发问,于是,2人就开始辩论,辩论的地点从课堂转移到操场,于是很多老师和学生在一旁观看。这有点类似今天凤凰卫视的“时事辩论会”节目。教学中这样宽松的环境,为中国后来造就一批杰出人才奠定了基础。那时的老师,把写文章看成一件很神圣严肃的事情。不像今天的学者,勤于耕耘,可又有多少文章是具有创造性的?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对最精彩的回忆留给了西南联大。何先生那一代人成长在内忧外患的年代,学人的理想都很单纯,那就是赶走日本鬼子,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单纯并不代表没有生机,单纯也不是简单的代名词。建国后出身的人,70后、80后更是无法体会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理想,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从《上学记》一书中,我触摸了70年前中国学人的理想和追求。近百年来,伟大的中国人一直都渴望自由,渴望解放,争取民族的发展空间。有思想、有理想的人,越在坎坷的环境里,越会振奋精神,积极思考。像何兆武这样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我们这片古老而焕发活力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