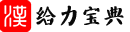别样
寒鸦掠过天空,划出一道道透明的伤痕。在这个冬季,琼花早已凋谢,明月掩了俏丽的容颜,只剩冷雪疾掠、冻云久凝,温婉的江南顿时化作冰寒的世界。
漫步在这别样的江南冬日,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三百多年前那个急雪翻飞的黄昏。
一个面容姣好的江南女子,青丝绾出精美的发髻,迎着飞雪寒风,婷婷地立在黄花堆积的院落,黛眉深锁,秋水般的目光中是无限的哀愁。夕阳下,昏鸦飞尽,雪湿衣衫,人,却还立在那里,不知那晶透的心上眉头正念着谁怨着谁。
漫天飞舞的雪,被黄昏的风吹入女儿的暖阁,翩飞如同春日的纷纷扬花。闺阁中隐隐飘散着极淡的苦香,是那支插在胆瓶中的梅,小枝分歧,如蟠螭僵蚓,孤削似笔,密集如林,那白梅胜雪,雪似白梅,在夕阳最后一抹余辉的照射下,显出一种寂寥空旷的美。但伊人却完全没有注意这些,她凝视着心形的香灰,那本是珍贵的心字沉香,经一整个茉莉开放的时节的打磨,沉稳如绵长的爱情。她看着成灰的心被风吹散,眼泪渐渐爬满了脸颊。
“昏鸦尽,小立恨应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她念着红笺上的词,想起了他烈火般的率性,还有那满腹的忧伤。“容若,你好吗?”她小声的问。“纳兰家的声名如此之大,又有几人知道他的心事啊?沈宛呀沈宛,你又知道多少呢?”她轻轻地摇头,提笔在红笺上写下了回词:“雁书蝶梦皆成杳,云窗月户人声悄。记得画楼东,归骢系月中。醒来灯未灭,心事和谁说。只有旧罗裳,偷沾泪两行。”那些缠绵的往事,亦真亦幻,而今心事无人可说,只有写在薛涛笺上寄于容若。
最为难处是无言。沈宛虽是才高人淑,终是汉家女子,又如何与纳兰家门当户对?好容易挨到最后,挨出了希望,两人的爱却早已遍体鳞伤。她只能眼看纳兰日渐憔悴,痛苦地挣扎。
终究还是相隔万重山,既要分离,为何要相遇?这种别样的哀怨与沈宛一起永远地沉入了岁月。
走在这江南的街道,望着这萧肃的江南,我的眼前,是一段别样的爱,别样的怨,化成这《梦江南》,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