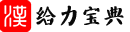【那些年】如梅在雪
生命,如果太纯粹,就未免单薄。
锲子:1977年的那场雪,格外的大,似乎在控诉着十年饥荒中的愤恨.文革在锣鼓喧天中的结束,无疑是给予了村子里的人们一个存活的契机。这原本是一个古楼林立颇有几分繁华的小村子,“破四旧”后,也只剩一片狼藉。
当黑暗吞噬最后一丝残阳的橙红,依稀飘雪的深空划出了一声哭啼,似乎要撕破长空。她,在所有人的失望中诞生了。在这样一个封建的村子里,对于已有三个女儿的爹妈来说,她的出生是有多不尽人意。
【一】
伴随着哭声的便是那“完了,又是个女娃”的叹息,如丧钟般渐远,也似乎如一个天大的包袱,压得那个倚在墙角的中年男子缓缓蹲了下去,点起了卷烟。
许久,哭声住了。
“这个娃就叫如梅,女娃娃都带个梅么……”中年男子吐了口烟,古铜色的脸上紧皱的浓眉在烟雾里模糊又清晰,微微颤抖的声音也越来越低,“女娃就女娃,谁让俺命里没有个送终的。”
“爹……”十六岁的香娃给她爹递了个眼色。他瞪了一眼,又埋头抽烟。香娃是他的大女儿,甚是乖巧懂事,一双丹凤眼像极了她娘。她把趴在窗子上偷看小妹妹的萍娃和老尕唤过来:“来,掸掸寒气,过会儿去看咱娘。”“大姐,咱娘生的不是弟弟呦。”还没等萍娃说完,香娃就用手捂住了她的嘴:“不要乱说话,听见没有,要不过会儿就不让你进去!”萍娃知趣得应了声“哦”。
“可是,大姐,娘生的就是小妹妹,我和二姐都瞅见了。”老尕打抱不平地说,忽而又摇着萍娃的胳膊蹦起来,“好啊好啊,以后我不是最尕了!”香娃无奈地摇了摇头,微微低眉,侧眼望着她爹。
“对,老尕说得对,你们娘就是给你们生了小妹妹,等那位大妈出来俺们进去看!”她爹倏地站起来,踩灭还没抽完的卷烟。
随着地上升起的白烟渐渐减少,香娃悬着的心也逐渐放下来。她爹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原是地主家的六少爷,如今在散尽家产后,也只落得低人一等。他也是个苦命的人,还没十五岁就死了爹娘。在他记忆里,他的爹娘也只是个带着高帽子,整天被拉在街上批斗的可怜人罢了。老六嘴里的嘟哝声好像从她记事以来就从没停止过。尽管她和妹妹的茶饭做得在村里都是出了名的,但老六还是会因盐放多了,醋调少了等小问题训半天的话。所以姐妹们对她们爹是又敬又惧,生怕做错一点儿惹怒了他。就连香娃的终生大事,也全凭老六草草地应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香娃不敢多言语,而每次看到爹失望的眼神,她也痛在心里,明白小妹妹的诞生对他及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就这样尽量的避免提及小妹妹。
“老六,又是个女娃,你又赔了……”房门还未开,刺耳的声音就冲进了耳朵,爹赶紧从上衣口袋但里摸出几张皱皱的毛票,香娃又娴熟的替他整理了一下后襟。她不难发现,这是爹过节时才穿的中山装,看来爹是对这个小生命充满了希望呢。房门从里边开启,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张妈那张嘴,厚厚的嘴唇咂着,不住地摇头叹息。
老六把钱塞进了张妈的手里:“麻烦你了,张姐,别嫌少哇!”张妈厚厚的嘴立刻抿成了一条线,嗓音又升高了一个调:“老六,你太见外了,这是我该干得么,哈哈!”她又拍拍老六的胳膊,“进去吧,好好养吧,先走了,闲了领上娃娃来俺家耍。”老六也附和着笑,直到张妈出了大门,他僵硬的笑脸才又绷紧。“真是非,生男生女关她啥事……”他又开始嘟哝。
“爹,咱进去吧!”香娃侧眼看着老六,谨慎地说。
“嗯。”
老六的声音似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也恰好可以被她听到。她扭过头,带有警告地对妹妹们说:“记住,千万别多说话。”
“为啥呀?”四岁的老尕满脸天真地问。
萍娃拉住妹妹的手:“大姐不让你说,你就别说,跟我后面,别乱动。”
“哦……”老尕嘟起的小嘴都能挂五个油瓶了。
她们跟在老六后面进了屋。迎面炉子旁坐着姑姑,心疼地抱着一个被棉褥裹得很紧的孩子。厚大的棉褥还是藏不住她的小,同老六的鞋底般大小。
老六示意姑姑把孩子给他,他轻轻地抱起了孩子,嘴里念叨着“如梅如梅”。看到孩子微微睁开了眼时,他竟露出了黄黄的牙齿。香娃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
“娘,娘你疼吗?”
“老尕,快过来,让你娘休息会儿。”姑姑轻声说。
老六也回过头,瞪了老尕一眼。
萍娃赶紧把她拉了过来。
“呦,听说又没生个男娃子哦,那个鼓励生娃的奖是白评了呦!”“就是就是,命里连个男娃都没有,老了埋都没人埋,哈哈!”一听就是同院的老四家赵云红和老七家王金花,仗着自己生了儿子,一唱一和的欺负老六家便成了她们茶余饭后的乐子。
老尕三步并作两步,把门关上,又倚着门。她幼小的身体如何抵得住两个女人,王金花一把就搡开了门。“啧啧,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还不让老娘进,啥教养都没有,也不知道你爹娘咋教你的。”
“要你管,疯婆姨!”老尕推开她,跑了出去。萍娃紧跟了出去。
老六放下孩子,眉头皱得更紧了:“老七家的,刚生完娃,你就别吵吵了。老尕是俺没管好,行了么?”
“老七,话说哪去了。” 赵云红捣了捣王金花的,“走走走,没看见人家在气头上吗?”她们溜了出去。
“耳根子总算清静了。”姑姑长舒了口气,又转头看了看她嫂英子,“哥,既然生下了,男的女的都一样,就好好养啊!”
断断续续的啜泣打断了谈话。“她娘,你别嚎了!”老六又点了一支烟。
“葛家兄弟,大坝倒了,队长叫你们去上沟呢!”听见门外的喊声和女人的嚷嚷声,老六就撂下一句“香娃,把炉子生好”头也没回,走出了屋子。
【二】
如梅出生后五个月,老六就出外了,也只有每逢清明和大年才会回来。
老六不在家的第二天,如梅病了。英子早上发现如梅浑身发烫,也不吃奶,心想着晚上回来就去看大夫。安顿好萍娃和老尕后,英子就带着香娃上地去了。
傍晚,踏着落日的余晖,她们回了家,放下铁锹,拉起驴车就往磨坊走。夜深了,英子才回来,刚扒了几口饭,就听见老尕在旁边屋里说“二姐,如梅是不是死了呢?”英子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扔下了碗,慌张地进了那屋,抱起璐菊就跑。“毛娃毛娃,睁开眼。”英子不停地摇着孩子,不断哭着喊。香娃也抱着老尕,萍娃提着手电筒跟在她后面。
终于到了卫生所,英子和孩子们用最后的力气敲门,“蒋大夫蒋大夫,开门救人呐!”将近一刻钟后,一个披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从“吱呦”一声开了的门内探出头来。
“是如梅她娘哦,这么晚了……”蒋大夫揉了揉眼睛,穿起他的白大褂,带有几分抱怨地说。
“蒋大夫呀,快救命呀,如梅一整天都没醒呀,救救她呀!”英子脸色苍白,还没等蒋大夫发完牢骚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孩子们也抱住大夫的腿,哭着哀求道:“大夫大夫,救妹妹……”
蒋大夫接过孩子。“快起来,你们这是干啥呀,我会尽力就她的。”他摸了摸孩子的头,翻了翻她的眼,又用听诊器划拉了好几分钟,“你早干啥去了?再晚来半小时娃娃就没了,肺都肿得呼不上气来了!”
“没办法,老六常年不在家,俺一个人带这么多娃,哪顾得了她呀!”英子啜泣着。
“无论咋的你也得管娃呀,现如今不是六七十年代了。”蒋大夫用药酒给如梅擦拭着身体,略带感伤地说,“那时候俺们连自己命都保不住,现在人人都能吃得饱……回去好好睡几天就好了!”他又在对面的药柜里抓了几剂药,“给,一天三次!”
“麻烦您了,蒋大夫。”英子摸着口袋,才发现来是走得太急忘带钱,抱歉地说,“对不住了,蒋大夫,明天再给您送钱来。”
蒋大夫微微笑了笑:“如梅她娘,你也不容易,就算了吧。”
“这怎么好意思……”
天刚亮,英子就让香娃把钱送到了卫生所。
“葛老六家的,队上调你家香娃去打水坝!”稍稍松了口气的英子,一听到如此肆虐的口气就来了气,却也不敢多说,只是缓缓地走到那人跟前,低声说:“大哥,能不能跟队长说道说道,别让俺们香娃去了,女娃娃家的……”
“哈哈,谁让你们家没男的,哈哈!”那男人大笑,笑得很张狂,像马嘶般,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消失在了英子的泪眼里,还有甩下的那句“连门儿都没有”如万根针尖的锋芒,成片的刺痛着英子湿漉漉滴血的心。
“娘,没事,俺能干的动。”香娃扶起蹲在地上的英子,“如梅和老尕我让萍娃照顾了,您就安心去上地吧!”随即,香娃就扛起铁锹,连走带跑的跟在男人们后面。
英子看着瘦小的背影在魁梧的男人们之后是如此的不堪,是啊,她好像也只有铁锹一般高。英子哭干的眼泪似乎又倒流成河,一股股直泻而下,打湿了衣衫。
艰难的日子里总是让人度日如年的,好不容易熬过了夏日农忙,又迎来了最最恼人的秋收,特别对于这样一个极度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来说。
眼看着深秋来了,别人家的庄稼都收完了,公家分给的地,收不完是不行的。英子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整天带着孩子们上地干活,哪里顾得上如梅。
深秋的天是异常的冷。
“娘,我冷,我冷。”一岁的如梅只上身穿了个没缝纽扣的夹袄,寒风中光着屁股的她瑟瑟发抖,蹲在地上抱作一团呻吟着。
夕阳西下,死气沉沉的太阳逐渐被圆圆的满月所取代,一阵阵阴风却与把夜照得似白天般明亮的圆月如此这般的不和谐,但更不和谐的是月下的哀嚎。
“娘,我冷,娘,我冷。”如梅已唤了千遍万遍,应和的也只有三个姐姐。
“叫你再喊!”英子疯了似的跑到如梅跟前,提起她的小胳膊,上前就往光屁股上抽了几巴掌,“冷不冷了,你再喊不喊了!”
“娘,不了不了,别打别打。”香娃阻止道。
英子也哭了,瘫在地上。“谁让他不是个男娃呢,你爹也不会走了。”
这哭声夹杂着怨恨,打破了这夜的祥和,也许这样的夜晚原本就深埋着人世间无法言喻的琐屑绮俗,早就失了宁静抑或就没有过安宁。而那群星闪耀的夜空,又迷惑着多少渴望平静之人呢?
【三】
日子一天天苍老着英子的心,将近四十多岁的她竟被世事折磨得骨瘦如柴,一双眼黯然无光,空洞出了沧桑。
老六破天荒的回家了,这使英子又有了些精神,不过也只是因为他娘死了。
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凑了几桌,请了些亲朋好友,也算是厚葬了。由于缺几升小米,就借了邻里王家的。事后,王金花来找老六。
“六哥,这老太太死了,平日里都是俺伺候的,你今儿个才来,这六升米你家还应该是天经地义地吧!”王金花靠着门边,两只胳膊交叉着摆在胸前,一副来势汹汹的样子。
英子搬了把凳子,走到王金花面前:“你坐,你要凭良心说话呢,我怎么没去伺候娘?”
“呵,哪只眼睛看见你去了,你分明想赖账!”王金花踢开凳子。
老六立在一边,平生最厌恶女人吵嘴,每次回家都会听到永无休止的吵声,像燕子窝里捣了一棒,比玻璃噌地的声音还刺耳恶心。
“本来就是,娘自然明白!”英子不服气地说。
“哈哈,人都死了,俺找谁公正去?不想还米,还懒死人!”
“本来就是!”
“你有本事把老太太叫醒啊?”说着,王金花就扯住了英子的头发。
“你欺负人,娘一直是我和香娃照顾的!”英子也撕住了王金花的衬衣。
“怎么着,打架呀!”王金花把眼睛瞪得像校场架起的灯泡般大小,活像只老虎,猛地扑到英子身上。
英子也不甘示弱,一手拽住王金花的胳膊,一手撕住几缕头发,使出吃奶得劲儿,仿佛要把这几年来的屈辱全部还给她,终于疼的王金花直叫“反了你啦,反了你啦!”
就这样两个女人抱作一团,打了起来。邻居老王闻声赶来,见状,也一时只顾发愣。
突然,老六像雄狮爆发般喊道:“都停手,不就六升米,六斗俺们都还,行了吧?”见两个女人没有停手的意思,老六冲到她们前面,捞起板凳,向英子砸去,嘴里叨叨着:“你也不听老子话!”。说来也命不该绝,英子头一闪恰巧砸到了王金花胳膊上。
王金花一屁股坐倒在地,躺在地上抱着胳膊撒赖,大哭道:“合起伙来欺负人喽!”
老王无奈地说:“米,俺家不要了,你就起来吧!”
“不行,打了俺就完事了,赔俺六升米!”
“行,赶紧滚。”老六吼道。
第二天,老六果真还上了米,又赔给了王金花六升。隔四间屋子都可以听到她笑了好些天,连做梦都被笑醒。为了这十二升米,萍娃被迫辍学了。尽管先生到家劝了好几次,老六也是“哒哒哒”的只顾抽烟。萍娃在套屋里哭了几个时辰后,也欣然扛起了锄头。
只是,英子精神萎靡,眼里光芒尽失。
而四岁的如梅也裹着香娃对象送来的衣服,原本穿在香娃身上就略有些大的上衣,如梅穿上就像唱大戏的一样,更像一个套子,套住了她一生的喜怒哀乐,她仿佛又如当年,吸不上起来。好半天,这种压抑感才慢慢消散。
【四】
都说春红太匆匆,如韶华易逝,也如少女难留。香娃二十岁了,应允出嫁的日子也快到了。
对方的媒人一遍遍的催着老六,老六也只是咂着烟。良久,才慢慢吐出一句:“明天,明天先让香娃见见吧。”
第二天,媒人就带着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到了老六家。男人手里的一大吊猪肉和两瓶酒使劲往老六怀里揣,老六也就没给他使脸色。
从那天起,香娃的眼总是红的。每每有人问起她的婚事,她都会摇着头哭泣。
联系QQ:320595451 QQ邮箱:32059545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