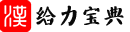被我叫停挖煤的人
在半个月前打手机给我二哥,他说他在红河,和村里几个人一起出去打工,做工的内容是修路,给包工头干。那我不反对,我相信事实上我和他是相互独立的,我不能反对他什么。
这时候我庆幸把我的手机寄给他,当时还埋怨,我给他手机,是想他经济紧张时,可卖两个钱,暂时解缓一下紧张,他倒好,去买张卡,用起手机来了。现在知道好处,我能直接联系到他本人。他告诉我他挺好的,出门之前,把家里的电话费交上了,如果想家,可以直接打回去,我嫂子和我爹都在家。
再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他问情况,他说好像干不成,有些要在前面做的工程没做好,他们还得等,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希望他出去外面看一看,这是好事,他在村里还是有威望的,别人服他,他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希望他能利用这种优势,做点农耕之外的事,对家庭生活有些额外的帮补。
昨天中午我再打电话给他,他讲了没两句,说是要睡了,晚上十一点钟上班。我问二哥,你不是在红河修路么,那地方也兴晚上修路啊。“那里干不成了。我在挖煤!”我一惊,同时心一酸,干什么我都没意见,唯独挖煤。“在哪里?是在圭山吗?”“是的。”我了解到,那是在一个私煤窑里干,晚上十一点下井,挖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
以挖的数量来计算,每矿车十五块钱工钱,每天可以挖三到五矿车,能挣到五到八十块钱,为了挣钱,他们当然会卖力挖,挖得越多挣得越多,期间不会有人要求像城里的双休日休息的。
“你不要挖了,赶快回去!”我说,“你不能为这了顶多一个月二千四的血汗钱干这个,干别的都好!这井下很危险!”“我知道危险,但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我已经干了六天了。如果不干满两个月,一分钱都拿不到,这六天就白干了。我好歹要干满两个月,把钱拿到再回家。”二哥说。
“你要注意安全。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全家人都等着你,你什么事都不能有啊。”我还能说什么?只有这样交待他。我一直控制我自己,在他们眼里,我永远都是小的。我自己也认为我不能去教训他们,不能去教他们做什么,去给他们讲道理,他们会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我挂了电话就打回家里,我二嫂接的。我说了他在煤碳山干活的事,她说她知道的,劝不住。我就说:“那些煤矿安全措施不健全,底下又有很多瓦斯等危险因素。那个钱是用命去顶着挣回来的,能挣再多的钱,也不要去!两个小孩正在上学。出点什么事,挣来的钱也赔不完!得不偿失!”
昨晚十二点钟的时候,二哥打电话给我。我问他:“这个时候你应该在井下呀!怎么打电话给我啊?”
“不干了,回家。”他显然还在抽烟筒。“屋头打电话来叫我回去。是不是你打电话回家说了?”我反作出惊奇的样子:“是啊,我打过,跟她们讲过我的看法。你决定不做了?”“不做了!明天就回去。”“跟人家打过招呼没有?”“打过了。”
我听到这话,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同时安慰一下他,“那六天就算八十块一天,也不过五百来块钱,算了,没就没了。你也没必要去冒那个险!”为了补偿他,我这时希望帮他找一点别的事做。
我说“没必要冒险”,是有缘由的。作为我的哥哥,甚至作为我身边的人,都是不容易的。
他早些年就挖过煤,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再去体验一次了。煤矿的事故不断,几年前我回家时,绕道师宗,在路上亲历一个情景:师宗离泸西近,有人到圭山挖煤,希望卖这种苦力来解决生活的困难。
然而,却因矿难死了,家里一个年轻的穷困的老婆,瘦得像根柴,本应漂亮的容貌却被布满灰尘和补丁的衣服、满脸的黑色尘灰及眼泪洗出的沟沟道道给遮住了,背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迎回家的是丈夫那洗都洗不干净的残缺的尸骸。
煤窑主给了他什么?几千块钱,能值一条命么?甚至它是不是那个人所干的全额工钱还是未知数!几千块钱,一条命,接下来的故事,这几千块钱还要被死者的在家活着的弟兄叔伯瓜分,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寡妇只有默默地,连哭泣都无声,这绝对让这家穷人更加没有生存的余地!一点都没有。还有的煤窑主为了掩盖事实,他才不管穷人的死活呢。反正煤矿死个人算什么?煤矿我是根本没去过,我也无法描述那矿里的情景,但我曾亲耳听二哥描述过瓦斯暴炸,使几十个矿工尸骨无存的情景。这个时候,我可不想跟二哥说这些,这多么的不吉利。
我两个哥都比我大很多岁。大哥在我还未上学前就和我们分家了。大哥二哥学习都相当好,却都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缀学。缀学后不久,二哥就去圭山挖了一年多的煤,不知有没有挣到两百块钱。只记得那时候,他中途回来看我们,总忘不了给我买一双鞋底前后翘起的运动鞋,我们形象地叫它“扳尖鞋”,而我舍不得穿,放到我妈的箱子里藏着,藏到我脚长大穿不了,我都不舍得穿。
我四五年级的时候,他又去挖了一次煤。那时候经过生活的洗炼,他后悔当年的缀学。家里面的经济难以为继,而且我还在读书,我在学校终于醒悟,学习好了起来,让他们看得到希望。为支撑家里的经济,他去圭山挖煤。人在煤矿,全家人都成日悬着一颗心,只有他回到家了,才全家高兴。
我六年级那阵,二哥的同龄人一个个都结婚生子了,照例,全家人都劝他结婚。家里穷啊,他说:“要供弟弟读书,弟弟哪天没读完书,我就哪天不讨媳妇。”他正是那样做的,直到我初三那年他迎娶了二嫂,二嫂嫁过来,婚礼酒席都没摆一桌,她也是位通情达理,娴惠的嫂子,我有幸生在这样的家庭。
二哥可以说是还是个孩子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小的时候,我家更穷得一塌糊涂,我一见天黑无光准哭,是二哥在堂屋里点着柴火哄我睡觉;我们吃饭只能吃两掺饭,即下面是米饭,只有一两碗,上面覆一层玉麦(包谷)疙瘩,米饭是一定要有的,我妈妈常去借米回来做,因为老大“就算饿死都不吃疙瘩,只吃米饭”,二哥和我就说我们喜欢吃疙瘩,疙瘩香。二哥才离开学校,我们就分家,他是家里除我爹外的重要劳动力。我们没什么经济来源,如果天时好,种的粮食刚够吃。种点瓜瓜豆豆的卖一下,得来的钱还不够买油盐。
我考取中专的时候,因是国家统一录取的“公费生”。看到录取通知书,全家终于松口气,一旦我成了公家人,这家里应该会松一点了,至少有一个儿子生活会好一点儿,父母亲也会心安。再看学费单,三百六十几元的学费,那就更松了一口气。
我平时都是在穿大哥二哥大表哥小表哥穿小的衣服,或者是特别疼爱我的舅母给我做的衣服。这次去省城读书,他们说不能让我再穿那些了,为给我买衣服的事也挺头痛。最后做了个决定,到了昆明,办好入学手续再说。把家里我妈养了一两年的一头大猪卖了,卖得九百几十块,全部准备给我,交了三百多,再除掉我哥回来的车费,还可以剩五百多,可以买衣服及留作我的生活费。
当二哥把我送到昆明的时候,才傻眼了,学费是三百多没错,还有其他杂费,一加就去掉了八百多元。买了面盆毛巾就才剩几十块钱,再除掉他回家的钱就没钱了。他一个劲地说对不住我,连衣服都买不起给我,连生活费都没了,不知道这几天我怎么过,他很内疚。
第二天清早,象石村九月的空气,凉凉的,刺在第一次到这里的人身上,有点儿生痛,生疼的还有我和他的离别情绪,一对骨肉兄弟的分离及在异乡的长期求学,同时也是我离开家的开始。二哥说衣服没法儿买了,也没有生活费,回家马上想办法弄来给我。
说完,他把他身上的牛仔衣脱了下来,套在我的身上。他仅穿件簿得像蝉翼的衬衫,在冷风中有些颤抖的双手扶住我的肩,说:“暂时只能给你穿这件了,这边还是有点冷呢!”“二哥,”我说:“有件事你不知道,我从四年级到现在,一共省下来两百多块钱呢,我现在带在身上,够我的生活费了,你不用担心。”
确实是如此,两百多块钱的零钱,六年来攒下来的,现在配上用场了。但二哥说:“那是你自己的。你听着,在这里,别的同学有什么,你就得有什么,别人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甚至比他们过好些。不要担心家里,不要给我们丢脸。妈妈担心你同别人打架闹事,自己注意不要和别人闹!”他就带着那二十来块钱,回家去了。
那件对我来说稍大的牛仔衣,我一直穿到快中专毕业。那时候一则是没衣,二则是不懂穿衣,冷的时候,我同时几件外衣加在身上,常被同学们笑话。
我们的生活在我读中专后的三四年间应该说是越来越难。有一年,我在学校得到家里的消息,说是二哥去砍邻村的竹子,整个人被扣了下来。这让我震惊,一向光明磊落的、有主见有魄力的人,居然做出这个事!
上天没给他太多机会,让他落在我们家,否则像他这样的人,早已出人头地,而不是被这样的困境永远纠缠着!问他的时候,他说事已发生了,没什么好说的啦。已经过去了,如不是走投无路,谁会做这个?只是砍了一捆竹子,被抓起来罚了些款,款还不起,还欠着。我这时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无论怎样,二哥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的高大!
我毕业后,家里的负担终于轻了一些,经济稍有改善。但家里他们住的房子,破旧得快倒了,房子一直漏雨,每次漏每次补,摇摇欲坠,多年前我回家就不敢登上房顶,生怕站在房顶,一不小心咳了个嗽房子都会倒塌。几次说重建,一直没建成。
直到二00三年,有一天夜里,雨水如注,半夜,我爹正在熟睡,一半土墙就倒下来了,幸好我爹是睡在离墙的那侧,墙体盖了一半床,雨水把它浇得像泥巴。二哥二嫂听到响声起来,看到现场我爹满身泥水,惊呆了。
二哥对我说,下定决心想把房子掀了,在原地重新盖一个,问我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可是我竟对他没多大帮助。他二00四年盖了房,欠下六万多元钱,至今没还清债。还有两个孩子,现在一个读初二,一个小学五年级。到处都需要钱,种烟烤烟这项经济支柱难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段时间去打工,去挖煤的直接原因。
我实在不希望他再去挖煤了,快四十的人了,不能再去冒这种险。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成器,帮不到他任何忙,否则,他实在无须再这样辛苦下去,无须再受这样的生活高压!年轻人,小孩子,受些苦是财富,但对于受过那么多苦的二哥来说,他不能再去受这样的苦,他真的不能再去挖煤,做什么都好,不希望他做这个。
他答应不挖了,回家,我由心的高兴。但在我写这个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到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