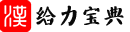【时间都去哪了】故土夕阳红 (自述文)
故土夕阳红 (自述文)
我的父亲膝下有五个子女,四男一女我是他的长子。村里的乡亲们,对他那饱经风霜的月历是历历在目的。
在父亲四十三岁的时候,共和国的制度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候我正在就读中学,祖母和母亲也还在世。在那个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年月里,尽管父母们一味地面对黄土背朝天,拼死拼活的挣工分,可总也糊不了一家八个人的口。而且,连年塌欠他人的帐眼儿纷至沓来,一年累一年地债台高筑,可谓之:年年补不住的帐窟窿;月月填不平的债水坑呀!
听村里长辈们说,我幼年时期的父亲,酷爱学手艺。像剃头、织网、编织、垒墙样样精通。特别是学拉弦子,最吃苦。当时家乡还没解放,家境特出贫寒,买不起弦子,他就自生办法。到地里瘸个高粱莛儿做弦弓子;搓条棉线做弦绳。做成后,就学着戏班里奏乐器的艺人模样儿,有么有样地在村里的荒草野坡中,一边为富人家放着牛,一边拉手中的弦子。时常如痴如呆地,陶醉于酷日寒月之中。
到父亲的少年时期,家乡解放了。村子的戏班改称为文化室。他不但常常到村部观看节目的排练,而且还默默地暗学拉弦人的技艺。在做弦子上又来了独创:削跟藤条做弓子;拽缕马尾毛做弓弦;砍树枝做弦架;割牛皮做弦绳。制成后,他就爱不释手与弦子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几经苦练,终于拉得有板有眼、绘声绘色的了。而后,就被村里吸收为文化室成员中的一员这是千载一时,他绝不失去这个机会。他天天早起晚归从不缺勤。
村里逢年过节时,就有文艺游乡会演的习惯他朴实无华也没有虚荣心,虽衣冠褴褛,可朴素干净,照样登台演奏。并投入沉醉、乐在其中。他后来,给我讲过一件令人痛心的故事。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因家境贫寒没新衣裳,他就赤身坦怀地裹上一件千疮百孔的棉袄,腰系草绳,穿上一件单裤片,光着赤脚就和村文艺队一道,敲锣打鼓地为村民们过节助兴去了。
深夜他在途归的路上,想象着家里的餐桌上应该摆放的美味佳肴:放桌上中间是盘美滋滋的年菜;桌子的一边是缸热乎乎的年汤;另一边则是香喷喷的年饭......等呀盼呀大年除夕终于来了,祈求一年的饱食一顿的希望,今夜将要实现了,美餐一顿,今夜那满腹的风寒一定会被热的汤饭驱散;还有那冻得僵直的骨关节肯定会被美酒舒展;那期盼一年的童心少意也一定会被年货满足......。然而,他一进家门,我奶奶便轻声地对他说:“我今个儿向你外婆家要来了几升秕谷,等明个儿对些野菜,咱一家老小可吃顿饱饭。”他听完我奶奶给他说的话后,又和往常一样,拿起那片陈旧不堪的烂套子,空着肚子去睡觉去了。
他的青年时代,正置“大跃进”的年月。村里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有了板车、自行车、缝纫机等人工机械。他得空就去观察去摸索机械的工作原理和部件构造以及在生活中的作用。揣摩好、学会后,就主动为集体和个人编车修车。顺帮村民们沾胶鞋、拼钥匙、拾掇手电打火机都是小事,连农村最初的有线广播和无线的收音机电子类的他都能摸索着修得来。后来他被派往,正在修筑的丹江水库工程工地上,为工地修理板车等机械服务。
当他不如壮年时期,正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日子。起初他有所顾虑,因为在大集体时期,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时任组保管的他,学会了烧砖窑的技术,帮了村民的起房盖屋和简单的吃喝问题。以此,竟割了他多年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并免掉了他的组保管的职务还检了讨。说以,他先是缩手缩脚地把集体分下的打面机支起来;后来试着买了台缝纫机和衣服锁边机;再后来他又购回一部补鞋机。在村邻街乡以补鞋、修伞、配锁补衣制衣等为业走村串邻的游动服务开了。挣得微薄小利,既此滋补了一家人的生活。
一年、两年、三年......十年过去了。政策真的没变,且越走越稳,他就胆子大了起来。把我送进了部队,指点我入了党。他辞掉了市剧团的高薪聘书,平心静气地尽自己特长,在家门口开了个车子修理铺,甩开膀子干了起来。
村里原有三个车修铺,父亲的铺子一开张就苦心经营、勤劳肯干、准时准地、加班加点、服务周到、廉价收费于一身,招揽顾客并竭力满足其要求,使顾客开心满意。说以,这些年只有父亲的铺子稳固常在,十分的红火。
我复员后和父亲一个院里住,时间一长便知道了他的作息时间表。冬天,清晨五、六点起床;夜晚零点左右熄灯。夏天,干完自家承包地活后,利用午休和饭后茶余来修车。他从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无论风晴雨雪,还是暑日寒月,村民随到随修从不无一家的事。他为人和善,处事公道被镇政府名为历年的遵纪守法和“五好户”。他进货要到八里外的镇子上去,一年四季不管天气的优劣,从不间断地往返于村镇之间的乡路上。一闪又个十年过去了,只见他有沧桑的人生月历,不见他有衰老的才智精力。编车扒胎、拆机好车,依然那么干脆利落、准确无误。经他的手,村民们生活中有了个可靠的着落,工作中有了个满意的喜悦。经他的手,村民们懂得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烧饭不用柴、出门不用鞋的道理和意义。
他有个好嚼,爱饮酒。三十年前,他到店上喝的是散酒且不就菜。如今他在家中喝的是瓶装酒,而且菜盘里是卤肉和俏菜。桌上另只杯里是上等饮料;膝上另只手里是过滤嘴香烟。平时他无闲言杂语,不声不响地把我们姊妹五人成了家、立了业;又不声不响地把我们二年内相继病故的祖母和母亲掩埋去;还是他不声不响地付清了祖母和母亲生前的医疗费。然而,在回答村民们的问话时,他至今还是那句口头禅:“这是政策允许啊!要是那些年我就是浑身的武艺,也养不活这家人呐!”。尽管他目不识丁,也理评了当今政策。
乔本占
二零一六年一月九日 写于乔湾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