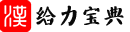我的睡眠史
太原
从一个接一个梦境中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变得明媚。我坐起身子,看着窗外的阳光像我曾经记忆的那样抵达到我的床前。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的事情可以想起来必须去做,或者,可以不做。我差不多忘却了所有的旧故事,在我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作为时光的附属物它们隐蔽起来。我还是有些懵懂,像仍在梦中一样。隔壁的邻居母女已经出门去了。八点多的时候,那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同她的母亲吵过一次架。我记得她们经常如此。只是我一直不明白她们怎么只剩了两个人,那个出走的丈夫,一直没有回来……
这座位于太原城北部的老旧楼房已经存在了许多年。我搬进来的时候是在夏季里。因为住在高处,所以屋子里很热。在这儿我开始生活到第九个月。看样子还可能继续住到农历二月中旬。我的生日前后。我不知道我会在哪一个明确的日子离开这儿。我的生日,像一段岁月的分界。
差不多是一个月前,我就准备搬家了。但一直没有决定下来。我在这里经历了一些事。夜晚里的睡眠,梦境中的奔跑,上午时分接到的无数电话。几次感冒。一部长长的爱情小说。许多时候的困惑和沧桑。我看到的理发店,音像店。秋冬季频率颇高的婚礼。那些沉浸在生活中的人。我的岁月从25岁延续到26岁。在这里,我还经历了几次长长的失眠。甚至,在一些时分,非常不自制地流下泪水。我发表过的文字,一些分行的断句,像我在白纸上记录的时光图谱。
在有限的休息日里,我观察过我所租住的这间屋子。贴在墙上的几幅明星照片,悬挂在那张宽大木床上方的节能灯,那个旧式木柜里所埋藏的秘密,房东一直不让开启的那一个巨大木箱。我甚至在小说写作中虚构到发生在这里的一个命案。我的思绪同贴在楼下的一张布告有关。是一个年轻女子死在了出租屋里。许多天后,那张布告已经被风吹散,像一个生命在空气中的消失,缓慢,但终至无形。
我在这里的睡眠其实深入而且安宁。只是曾经,有一种超常的情绪弥漫在那些一个人的夜间。
睡眠之前之后的多数时分,我可以领略到一个人居住时的那种巨大寂寞和恐慌。我倾听到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无论是在喧哗的早晨还是正午,都有一丝丝淡泊和宁静围绕在我的身周。这是我在许多年前所盼望过的。在原先的群居生活中,我积累过对独居生涯的巨大热情。但随着时光的递进,我觉得自己正在朝一个未名的方向去。在很深的睡眠里,在我不用手机的十天中,我从我白昼里所置身的日常生活中被剥离出去。我在一个人的睡眠中与这个世界仿佛全无关系。在漆黑的夜色中,我有时睁开双眼,有一束更深寂之处的目光,与我安然地对视着。
乡下
我几乎没有一次比我的母亲起得更早。她总是在先于我入睡的时间准备睡去。当我在灯下看书时,隔壁会传来她的催促声:该睡觉了,孩子。我的父亲,他的呼噜声穿过墙壁的缝隙响在我的耳际,他的声音中没有疲惫,只有深长的时间像在他的睡眠中打着鼾。我总是多么奇怪,作为一个五十岁的人,他的睡眠太多了。
我的幼年时光是在乡下度过的。那些纷繁复杂的梦境,有一个简单而宁静的乡村背景。许多年后,我常常想起我家的旧院子。风声肆虐的冬夜,院子里的树木哗哗作响,让人有一种置身树林中的新奇感。我经常在浅睡时分察觉到院子里寒冷的狂欢。许多年……这种感觉一直未曾消退。或许是,当我在那间窄小的屋子里安睡时,我就想到,我会把记忆作为一个容器,有为数众多的秘密在它的腹部深藏。
院子很大,住着一大家人。每逢早晨的阳光降临,当我从屋子里出去,会有年龄不等的堂兄弟姐妹们在窗前聚集。这一天还有些早。他们说,到哪儿玩去?
是啊,到哪儿玩去?一直到今年春节回家,我仍然听到了这种询问。几个十岁不到的小孩子等着我的回答。他们都叫我叔叔。我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全。我看着他们的脸孔,依据早年对他们父亲的印象判断他们各自是谁的孩子。他们看着我在早晨的阳光下走神,然后仍然一齐喊出声来,走吧。走吧。叔叔。我爸说,让你带我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由于年少时太熟悉了,所以经过此后多年的分别,此刻重聚,依旧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心头滚动。除了比我大几个月的最小的堂哥,别人的年龄我至今仍然不太清楚。是在转眼之间,我们站在了一个水平线上。只是,他们说,你也该成家了吧。我们在你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孩子都像你当年那么大了。来,来,喝酒。
我在夜里想着这些事情。我在深夜里,对自己的所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这么多年,我已经无法把家乡当成惟一。或许原本不是。我对它的陌生感那么浓重。除了依稀可辨的几棵枣树,我曾经的居所几乎无法看出当年的半点痕迹了。我在想着自己是怎么生活在这儿,十五年或者十六年。我还想着我是怎么离开,以后又怎么回来。似乎无迹可寻。当我在或不在的时候,这里都在潜移默化地变更着。我当年看重的人与事,转眼都变得那么遥远了。许多老人,也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每一次回来,母亲都会告诉我,谁谁谁不在了。我站在屋子中央,偶尔想一下从前他们的样子,更多的时候,我仿佛没有听清似的。过后许久,才向母亲发出质疑,是谁呀?
母亲嗔怪地指着我说,什么是谁呀?跟你仔细说话的时候总是不听。
我在乡下的睡眠充足。深夜时分,多半是我最宁静的时刻。白天里琢磨不定的事情,此刻都游走到一个我不曾到过的地带,偶尔在梦中出现,也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我在梦中几乎离童年很近了。我的爷爷和奶奶,都像我十岁时记住的那样。他们没有告诉我,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他们先后去了另一个地方。而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存在过的,人间最深刻的别离,在梦里,只是呈现出朴素的灰白色……
十九岁
我难以忘记的十九岁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你所知道的,所有的事件只有成为往事时才具备这种特征。我一直记得那张折叠沙发。把它铺开后就是一张床的样子。我在夜里睡在上面。
是十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里,我经历了毕业离校后最初的一段光阴。
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整个白天里,市报社的六七个人就在这里办公。我坐在靠门的那一张椅子上,有时还会挪得靠里边近些。我的对面,一位尚属年轻的同事已经开始秃顶。他大约二十八九岁,曾经有过漫长的调动史。是在此前一年的时候,他在乡下教书。每天往返于十多里的乡间公路上。他讲起在市教育局局长办公室里的静坐,抽着烟(他平时基本不抽),看着袅袅的烟雾在空气中飘移,他说,像一个人的命运无所依傍的舞动。
他的样子有一种事过境迁的好笑和沉稳。他自己也有一种安定下来的淡漠和沉稳。市里的女宣传部长指着他的秃顶,开着玩笑:
一个年轻的老干部。
我看着许多人进进出出。像刚刚来到一个自己意料之外的时间的局部,我有一点点失措。办公室里经常有人在谈笑。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许久。我看不到自己的命运在何处。
报纸一周一期。上班时并不忙碌。每个人的面前放一杯茶水,时间在喝茶聊天看报中缓慢流逝。
能够保留下来的时光都跟夜晚有关。我的情绪跟夜晚有关。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十九岁的人到底有多少可以叙说的人与事。是在记录和回忆着而不是其他。舍此,我一直不知道我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秋冬季的风声和季节的寒冷交织在一起,屋子里的宁静和喧闹交织在一起。现在仍然想不起来的故事,在当时或许并不存在。但总有一种奇怪的声音隐藏在暗处。办公室里只我一个人的时候,整整一层楼,也多半是我一个人。只有稍下的一层楼里,市委和市政府的秘书们多半还在忙碌着,仿佛永无止歇。
我的时间开始变得轻盈。我在深入的阅读中开始变得轻盈。在此前此后没有经历的那种岁月,在当时成了一个惟一。我独自拥有的那些夜晚,那些夜晚里的孤独和忧伤,仿佛只属于十九岁的时候所独有。
有时我看电视到很晚。这样的时候困倦像刚刚来到我身体中一样被我发现。因为害怕睡下后并无睡意,所以一直固执地在电视节目中流连。那深夜里的舞蹈和音乐,很多年后依然被我记住。屋子里的灯已经被我拉灭,只剩下电视屏幕上的光芒在闪闪烁烁地浮现。偶尔我就那样漫无目的地睡去,半夜起来,发现屋子里有声音在响。抬起眼来,有局促而黯淡的彩色的光。我的眼睛里已经有梦的色彩,它们与屋子里存在的事物交织在一起。我把被子裹紧了些,片刻之间有些失神。我有一种来到异乡的真正错觉。那遥远的女子的脸,她在深夜里的无尽的欢乐,以及,她回过头来,在超不过三米的地方那妩媚的一笑,就那样进驻到我的心底。我把电视关了,她依旧留下来,在暗寂的夜里,只有她将头部的薄纱轻轻舞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