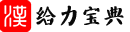冷落小店
(一)
好多年前的一个秋天。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里要搞开发,说不定会有好生意做。
我似乎又此话所动了,第二天一早我就有心转来,可当我看到那布满泥泞的道路和那如此宽大却无有寥寥几辆车停放的某某大型停车场,我的心就凉了半截,我想这能成吗?再看看那冷落稀疏行人的大街和那一座座老广式的土屋,我那只本想做点小店生意的心倾刻荡然无存。随后,我虽然在此村一端有过一些短住,虽然这里也建起一个所谓的小小菜市场,也许是因太小的原因吧,所以也很少来,即使偶尔一次也无有任何印象,再后我就搬走了。
(二)
恍惚间,一年多过去了,一年后的我又来到了这里。我不由惊呆了,因呈现在我眼前的一切变化太大了。是的,不必说那布满泥泞的道路己被那水泥和石子的混合物所代替一一平而坚硬;也不必说那原为空旷的车场上己停满了各种型号的长途货运车并又前后扩建了两个大型停车场;就单说那原为土制的老屋和那稀疏行人的大街,己是高楼林立,车辆匆匆,人流济济就足够让我知道这里己是繁华的了。
不知怎的,我不由后悔起来,后悔我当初不该犹豫;后悔我当初没有租下房屋;更后悔现在想租也租不到合适的了,也许是因我太嫉妒别人发了财,也许是因我太心切的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不顾一切的在一个即偏僻又偏远的衔道,租下了一间较为简陋的房子。
(三)
就这样我的综合小店在无声无息中开始了:士多、书、碟片。记得我开张的第一天,就有一帮手提所谓装有香皂、毛巾的方便袋,身穿好像很多年未洗的大裤衩,脚踏似乎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的大拖鞋,有点日本进村式的,进门便问:“有黄碟卖吗?”听音色好像北京以北的。
“对不起,我这里不卖这个,”我微笑着说。
“操!那你凭什么赚钱。”
随后就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司机,跑长途拉货的,你不要小看这些司机,说话很粗鲁,可对这里贡献可不小。你听说过十个司机九个坏吗,这是真的,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特别是嫖,走到哪里就嫖到哪里,车上、车下,车里、车外,旅店里、发廊里,餐馆、小食店。无所不到。就算五天嫖一个,五十天就有十个,五百天就有一百个,这一年不多说六七十个总有吧。这是北京以北的,北京以南的,北京以西的,北京以东的,河南、山东的,山西、陕西的,湖南、湖北的,浙江、安徽的,新疆、内蒙的,四川、甘肃的,江西、广西的等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这里都有,你说要有多少个司机,需要多少个妓婆,就单说这个村,多了不说,成千上万总有吧。
你知道吗,有妓婆就有烂仔。这不,偷砸抢的,吸毒卖粉的,小商、小贩也来了。所以司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商机,哪里就会发财。这不,开餐馆、旅店的,开发廊、小店的,开商场、卖小菜的,开诊所、性用品店的,小摊、小点就更多了。不然这里能发展这么快;不然这里会有这么多高楼大厦;不然这里的人会这么有钱,多了不说,几万,几十万总有吧。你知道吗,这是他们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过的讶!我愈来愈想,原来我这滴滴小店也不由中受益于这所谓的司机,妓婆了。
(四)
小店一天天开着,尽管地方偏僻,简陋,也许是因人多财兴的原因吧,生意便一天一天好起来。心里高兴极了,傍晚时分,间或便去那所谓的大街上走一走,转一转。脚踏和遥看着那布满霓虹的大街和那远方高楼上所释放出的光,我似乎这时才发现这里的晚间比白天更迷人:是的,不必说那大街、小巷上,商场、小店旁;也不必说那餐馆、旅店里,发廊、性用品店里;就单说那小摊、小点旁就足够让你触目惊心的了。
有吃有喝的,有哭有笑的;有柔声细水的,也有暴跳如雷的。稍远看:有游手好闲的,也有疾飞奔跑的,车辆匆匆,人声鼎沸,无不热闹。偶尔你还能听到一串串所谓的歌声。尽管有的像野猫发春,驴哭狼叫,但总给你一种生活的气息。这就是改革,这就是开放,这就是南国,这就是全国各地四面八方都来你讹我诈,你争我夺的淘金之地。
小姐出动了,像星星,像月亮,姹紫嫣红的。我原以为是什么机关秘书,商场售货员,扩台小姐,原大都是妓婆,靠出身卖淫的,发廊里,旅店里,大街上满是的,有的还走啊走!
小伙子们也出来了,趾高气扬的,像是刚从前线打仗回来的将军。也有摇头晃脑的,像旧社会恶霸地主的崽子,惹不起,也碰不得。我原以为是什么国家干部,企事业主管,原大都是烂仔。靠偷砸抢,盗买盗卖,敲诈勒索度日。有人说他们大都如虎似鼠,白天休息,晚上出动,轻的给钱便吧,重的则乱刀捅死,呜呼!无法可想。
(五)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延伸,我的小店生意也愈来愈好了。熟人也慢慢多了起来,租书、租碟的,在此打电话、打扑克的,也有谈天说地的,记得有一天有个熟人说她那里有一个村已形成了花赶趟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丈夫领着老婆的,母亲领着女儿的,姊妹一块的,看谁会卖淫,看谁挣钱挣的快,看谁挣钱挣的多,看谁先盖起那名副其实的小洋楼。我清醒地知道,中国的公民大都以贞洁为重,怎么转眼间他们大都成了改头换面的人,再不觉得卖淫是一种不可告人的事了。
记得还有一个小姐说,她是她表哥骗出来的,其初说是出外打工,到了才知是逼她卖淫,不卖不行,就这样一边卖淫,一边和表哥同居。也许是有钱的原因吧,最后表哥又在家物色了一个,显然是作老婆,并且是处女,这下可把表哥乐坏了,他说他这样可以把老婆领出来,先让别人跟她睡,他说这样可以得到一批处女开苞钱。
对于她们的话我是有点不大相信的,天底下哪有这种事,这不是畜牲吗,直到有一天有个很熟悉的大姐带着她那还未高中毕业的侄女出来开处女苞,并且高兴的不得了时,我才相信,这种事不但有而且很多。
可担心害怕的事也来了,某某某司机被烂们敲诈勒索的不敢吃宵夜了;某某某女孩被妓头逼得跳楼自杀了;某某某被烂仔乱刀砍死了;某某某手机被抢,车被盗了;某某某……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看书,忽听一阵阵喊杀声,抬头一看,几个彪形大汉正各持一把手枪,追赶前面那个奔跑的人,砰砰……几声枪响,那人索然躺下。看得清那人满身是血,地下还流了一片。起初我以为是什么公安便衣再追呜枪不止的盗贼,随后便知他们大都是烂仔,是黑吃黑。
(六)
也许是因这一切的一切,一天傍晚忽听一阵阵警笛声,并且愈来愈大,似乎要撕碎这迷蒙的夜空。随后便传来一阵阵呼啦啦的拉门声,邻舍告诉我马上拉门,一时我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慌忙中拉下门。跑到大街上,才知这里好似大难临头是的,东奔西跑的,左躲又藏的,如同热锅里的蚂蚁乱糟一团。接着我便看到一帮:头戴钢盔,脚蹬高靴,手握钢枪,身穿防弹衣的人,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防暴队。
我似乎这时才分清这就是防暴队,那就是民警,那手拿铁棍,身穿公安不公安,保安不保安服装的就是护村队。随后我便知道这是黄、赌、毒大扫荡。尽管有的人东奔西跑,东躲西藏。尽管有的发廊早有警觉,可还是抓了一大把,大车,小车满是的。有哭有笑的,有济有叫的,还有的在不停的与外面的人打招呼,要朋友帮他怎么怎么的。一时我好激动,好觉得大快人心。可不久又来了,又是这样骚动一阵。不知怎的,竟三番五次,五次三番来,最后我才听说这里已划为重点,市内出了名的黄、赌、毒地方,杀人肇事点。
似乎我这时才发现小店的生意愈来愈差了,租书、租碟的少了,打电话、打扑克的少了,谈天说地的也少了。好多人告诉我他们也要走了,并说这里的城郊结合已过去,新的城郊结合又在开始,他们要到新的城郊结合地方去,说那里属于三不管地带,那里很好混。显然小店生意一天天差了下来,再看看周围大街小巷:空店,转店的很多,我知道生意做不长了。
随着一次次的大扫荡,我便知道村里已少了很多人,但也知道了一些关于大扫荡背后的一些传闻。有的说:某某某发廊抓了,某某某还在开着了;某某某旅店去了,某某某旅店就没去了;某某某烂仔抓去了,某某某烂仔还在和治安吃宵夜了;有的说这样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不解决根本了;有的还说这是公安的收入,靠此赚外快了。
对此说法我似乎有点不大相信,听说他们大都取之于民,大都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怎么会亏对人民呢!
(七)
尽管如此,我还是愈来愈觉得雷锋少了,坏人多了,专门利已代替了大公无私;公朴少了,害群之马多了,贪官污吏取代了无名英雄;高楼大厦多了,富人多了,拾金不昧却成一种傻瓜才做的事;烂仔多了,妓婆多了,抓奸不在是光荣,而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我也愈来愈知道我的脾性也愈来愈坏了:愤怒多了,憧憬少了,渺茫代替了理想;恭奉少了,疾骂多了,烈性改变了温柔;金钱不在是奢侈,老板不在是羡慕;妒嫉变成了仇恨。
小店还一天一天开着,大街由繁华到冷落,由匆匆到稀疏。生意也愈来愈无人问津,水电便宜了,房租降了,可还是无能维持。
一天一个精通时事的人告诉我:搬吧,还是搬吧!妓婆少了,烂仔走了,司机不在出来,你还做谁的生意。你知道吗?妓婆不可少,烂仔不可无,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妓婆就像马路边的厕所,菜里的味精,没有她那南下十万大军建设者,就会被憋得抓耳挠腮,生活暗淡无味。烂仔虽烂也不能无呀,就像那下山猛虎,虽要吃人,可也得保护呀!看着精通者的远走和那稀疏行人,再瞧瞧我这冷落小店,我依在想:她说的对吗?我不由模糊起来。
(八)
……
好多年过去了,为了生计,我早已从那所谓的文明之城搬到了S城,从S城搬到了B城,从B城搬到了SH城,又从SH城搬到了W城。不知怎的,不由中我便想起它来,我想,现在总该好多了吧!几经辗转告诉者告诉我:变了,这里早就变了,摊点少了,防暴队不在来,发廊变成了按摩店,吸毒暗哨变成了《休闲会所》一一合法了。